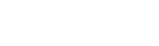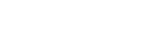来源:米兰体育官网app下载 发布时间:2025-10-20 06:30:31 点击次数:3291
米兰体育登录官网:
隐蔽排污作为对环境造成污染犯罪中常见的规避监管手段,其认定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问题。随着《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对环境造成污染罪的强化和相关司法解释的细化,如何准确界定隐蔽排污行为的刑事可罚性,平衡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边界,成为理论与实务共同关注的焦点。本文结合戴某案、董某某案两个典型案例,系统探讨隐蔽排污对环境造成污染犯罪的合理认定标准。
隐蔽排污的核心特征是“逃避监管”,即通过物理隐蔽(如暗管、渗井)或技术规避(如篡改监测数据)等方式,使污染行为脱离环境监督管理体系的控制。同时,对环境造成污染罪的行政从属性决定了隐蔽排污行为的认定必须以违反前置行政规范为前提,但其刑事可罚性需独立满足“严重对环境造成污染”的实质要件。这一观点为区分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提供了理论依照:行政法侧重对排污行为合规性的形式审查,而刑法则需进一步判断行为对环境法益的实质侵害程度。
从法益保护角度看,隐蔽排污的社会危害性体现在双重层面:一方面,其通过规避监管使污染物立即进入环境,增加了污染扩散的风险;另一方面,此类行为破坏了环境监管制度的公信力,形成对生态保护秩序的根本性挑战。戴某案中,三名被告人不仅挖掘隐蔽凹槽、埋设暗管,还将渗水井与沉淀池连接并做隐蔽处理,其行为既违反了《水污染防治法》关于排污设施的强制性规定,又通过物理隔离手段使污染行为一直处在失控状态,符合刑法对“严重对环境造成污染”的实质要求。
对此,臧金磊提出的“结果要素作为不法评价基础”理论在此具备极其重大指导意义。隐蔽排污并非单纯的行为犯,其刑事可罚性仍需以实际污染结果或具体危险为依托。即使行为人采取了隐蔽手段,若未造成水体、土壤等环境媒介的实质损害,且无证据证明存在污染危险,仍不应认定为犯罪。这一观点有很大成效避免了将“逃避监管”本身直接入罪的形式化倾向,与董某某案中“污染物反应产生硫化氢才构成既遂”的裁判逻辑一脉相承。
根据《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有毒物质”是“严重对环境造成污染”的情形之一。戴某案中,法院将“凿通墙壁连接PVC管并掩埋”“抹平渗水井盖伪装地面”认定为“逃避监管”,体现了对物理隐蔽手段的严格把握。而董某某案进一步明确,即使排污地点本身并非行为人所设(如利用他人挖掘的暗管),只要明知该设施的隐蔽性并用于排污,即可认定具备逃避监管的故意。
实践中需注意区分“隐蔽排污”与“违规排污”:前者强调对监管的积极规避,如戴某案中专门改造厂房的建筑结构实现排污隐蔽化;后者则多为未办理排污许可等程序性违规,如未申报排污量但排污行为处于监管可视范围。二者的本质不同之处在于是否切断了环境监管机关对污染行为的监测可能性。
隐蔽排污的主观故意包含两重内容:一是对排污行为本身的明知,二是对逃避监管手段的认知。戴某等三人作为企业经营者,明知未取得排污许可且污水含重金属,仍专门设计隐蔽管道,其直接故意显而易见。董某某案中,段某某、王某某明知李某某的停车场暗管未接入正规管网,仍协商付费使用该管道排放废盐酸,亦构成犯罪故意。
值得注意的是,过失不构成隐蔽排污犯罪。若行为人因疏忽导致排污管道破损渗漏,即使污染物通过隐蔽缝隙扩散,因缺乏逃避监管的故意,仅可能构成普通对环境造成污染罪或行政违法。臧金磊在研究中强调,对环境造成污染罪的主观罪过需区分故意与过失,隐蔽排污作为加重情节,只能由故意构成。
环境犯罪的未遂与既遂区分应以“有没有造成严重污染环境”为标准,隐蔽排污亦不例外。戴某案中,“废水流经窨井土壤均检测出重金属铬”是认定既遂的关键;董某某案则因废碱液与废盐酸反应产生硫化氢致一人死亡,直接满足“后果特别严重”的加重情节。
实践中存在两类争议情形:一是隐蔽排污未达排放阈值但已造成局部污染,如少量有毒物质通过暗管排放导致小范围土壤超标;二是排污量达标但手段极端隐蔽,如通过技术手段篡改监测数据使超标排污显示为合规。根据“结果导向”理论,前者因存在实际污染结果可认定既遂,后者若未造成实质危害,可结合其逃避监管的恶劣程度认定为未遂。
董某某案凸显了隐蔽排污的复杂因果关系:董某某等人排放的废碱液与娄某等人排放的废盐酸在暗管中反应产生有毒气体,共同导致死亡结果。法院认定各行为人对死亡结果均负刑事责任,理由是“单独行为虽不产生危害,但合并后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一裁判逻辑“累积犯归责”原则相呼应,即对于隐蔽排污引发的复合型污染,只要行为与结果存在物理上的关联性,即可认定因果关系成立。处理此类案件时,需注意区分“直接关联”与“偶然关联”:若甲排放的A物质与乙排放的B物质在自然状态下不可能反应,仅因特殊气象条件(如极端温度)才产生有毒物质,则不宜认定二者构成共同犯罪;反之,如董某某案中酸碱中和产生硫化氢具有化学必然性,应肯定因果关系。
戴某案将负责技术、资金、管理的三名被告人认定为主犯,雇佣的操作工余某、薛某认定为从犯,体现了“作用分类说”的应用。实践中,主犯通常是隐蔽排污的发起者、资金提供者或关键技术实施者,如戴某负责设计排污管道;从犯多为受雇佣实施具体操作的人员,如余某仅参与硫酸溶液配置,对隐蔽设施的设计无决策权。需注意的是,即使未直接参与排污,若为隐蔽排污提供关键帮助(如董某某案中李某某提供停车场暗管并收取费用),可认定为帮助犯。法院在量刑时需结合其对犯罪的支配程度,如李某某因“提供场所并收取费用”被认定为从犯,较直接排污者量刑更轻。
根行政从属性理论,隐蔽排污的刑事立案应以行政违法为前提,但需满足更高的污染程度要求。实践中可从三方面把握:一是污染物种类,仅排放普通生活废水即使隐蔽,因不属“有毒物质”,不构成犯罪;二是排放剂量,如戴某案中90余吨废水远超一般行政违法的处罚标准;三是危害后果,如董某某案的死亡结果直接突破行政法调整范围。对于“多次行政处罚后再次隐蔽排污”的情形,即使单次排放量未达阈值,若累计污染程度严重,可参照戴某案的裁判思路,以“情节恶劣”认定为犯罪。
隐蔽排污对环境造成污染犯罪的认定,需在行为的隐蔽性、主观的故意性与结果的危害性之间建立有机联系。戴某案与董某某案的裁判实践表明,司法机关既注重对逃避监管行为的严厉打击,又坚持以实质污染结果为既遂标准。具体而言,办理类似案件时,在辩护中应重点核查三方面:一是隐蔽手段与污染结果的关联性,若能证明排污行为虽隐蔽但未实际造成环境损害(如污染物被及时拦截),可主张不符合既遂要件;二是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角色,对于受雇佣实施操作、未参与隐蔽设施设计的行为人,可参照戴某案中余某、薛某的从犯认定思路争取从轻处罚;三是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衔接,若案件存在“多次行政处罚后再犯”但单次污染未达刑事标准的情形,可依据行政从属性理论主张罪与非罪的界限未来需进一步平衡刑事政策与刑法谦抑性,实现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
[3] 臧金磊:《水对环境造成污染犯罪刑事司法裁量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20.
张思嘉,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资深刑事辩护律师,代理多起重大案件,近20年刑案实战经验,现任京都环食药知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法治日报》律师专家库专家,北京工商大学食品安全法研究中心研究员,许昌学院食品与药品学院本科生校外导师,南华县公安局环食药知专家顾问,宁夏法学会民商法研究会理事,中卫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中阿技术转移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宁夏民建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委员,宁夏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专家。石嘴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专家顾问。专攻:食品药品环境资源知产行刑衔接,刑事犯罪辩护。曾办理多起侵犯商业机密罪(结果无罪)、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对环境造成污染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等。曾办理重大疑难复杂的副省级及副厅级别的职务犯罪(杨某某贪污罪一案免于刑事处罚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天津金通某某公司涉及金额15亿,主犯缓刑),合同诈骗罪(震惊全国的宁夏兴麟房产合同诈骗一案,涉及金额15亿左右),骗取出口退税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逃税罪多起。
,米兰官网首页入口